发布于
【川藏记忆】第一站——拜倒在四姑娘山的石榴裙下 [复制链接]
精彩话题推荐
文字型--------------进行中
#杭州身边事#【杭州1男子穿短裙踩高跟惹争议】昨天,@街拍滚叔更新了街拍:一男子穿短裙,踩高跟鞋。并配文:尊重身边每个勇敢做自己的平凡人,为他手动点赞!网友声音:A:男的穿成这样,看着就不舒服。B:不
文字型---------------------已结束
大多数早期的回归研究都不报告样本外实验中方法的可预测性。传统地来讲(Cumming et al. 2002),R2或修正后的R2是作为评估预测模型的措施,但他们的使用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,这在我们看来是
图片型投票--------------已结束
片中,吴亦凡饰演一个家境殷实的好男儿——程铮。他人长得帅,球打得好,又是学霸(数学100分)一枚,自然就成了校园的风云人物。与同为学霸又是班干部的班花组成一对,既悦目又怡情,频频招来众人艳羡的目光。程
呵呵哒
哈哈哈哈哈哈哈fh人外人顶顶顶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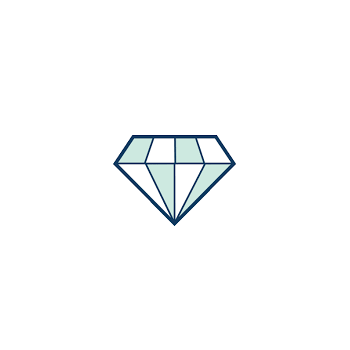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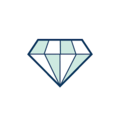
所有的城市在我眼里并无大异,哪怕是被冠以诸多美誉的成都。作为西行的中转站,在已安排好的成都军区招待所住了两天,一天用来吃美食,看美女;一天用来补给路上所需的食品和药物(事实证明,那些士力架和必备药品在往后的路途上给了我走下去的力量)。
藏族司机卢老七一大早来接,丰田霸道的车里满满的塞了七个人,除我之外,还有三个重庆来的大哥大姐,也要去四姑娘山徒步;另外三个大概是卢老七的老乡或亲戚,都是一路上在不同地点接到的,手里大包小包拎着进城购买的物品。坐在这样的车里,任凭盘山路有多少道弯儿,都不用担心被甩出去。我很好奇一个藏族血统的人为啥姓卢,绷不住了问卢老七,他告诉我说:他爷爷是广东人,年轻时跟随革命队伍走长征,因为生病留在了日隆镇,不曾想因祸得福娶了个藏族姑娘。当他得知我也姓卢时,亲切的称呼我“小卢”,我叫他“七哥”,我们之间这样带着一种陌生的利益关系,也有了些许人情味儿。
到达映秀前后的那段路况是最差的,时隔三年,依然能看出这里遭受的重创。车子在搓板路上颠来颠去的样子一定像只笨重的簸箕虫,我们这些“五脏六腑”被挤压在一起。漫长的路途上七哥每讲一个过时的笑话,自己先笑得前仰后合。翻越5040米的巴郎山时开始下雨,然后铺天盖地浓的化不开的雾气突然间劫匪一样冲出来,三米内看不到人,车子似乎被推着一点点向前挪动。不记得走了多久,我们从这混沌里瞬时穿越到一片明朗中,身后的雾气悠然泊在山坳里,浩荡的云海以这样一种魔幻的形式第一次突现在我眼中。只要我弯下腰抓一把,就是甜丝丝的棉花糖;只要我毫不费力的吹口气,就是漫天的蒲公英;而只要我轻轻一跃跳下去,那就是一段在云端的日子。
八小时后到达日隆镇,在卢老七的客栈安顿好后并未感到不适,高原的日头也不急于落山,于是我溜达着去了传说中的“冰石酒吧”。男主人唐炜曾是风靡成都的重型摇滚乐手,女主人是做平面设计的,夫妻两人于2008年来此旅行后决定留下来,于是就有了这座开满格桑花的小院落,还有三只性格迥异的大狗。我去的时候男主人正在院子里鼓捣木刻,一边云淡风轻的跟我聊天,一边干活儿。谈起音乐,他的兴致便来了,用那把跟随多年的吉他为我弹唱许巍的《旅行》。他不用手机,用最原始的手摇电话和邮箱,让生活慢悠悠的跟着自己的调子走。我在那里逗留了很久,直到漫天星光浮现,七哥才开车把我接回去。
次日清晨,带了两瓶水和简单的食物,伴着细雨与重庆的大哥大姐一同去往四姑娘山长坪沟徒步,全程29公里。前边很长一段路都是木板铺成的栈道,走起来轻松惬意,像公园的观光客,缺少一种原始的硬朗。我走得很快,我急于走到泥泞中去。
像是一座被施了魔法的丛林,到处都是绿色。被宝石绿的河水经年累月冲刷的石头也泛着绿光;深绿浅绿的树木织成一张密不透光的网,给予葱绿色的青苔隐秘生长的空间;黛青色的群山隐藏在云雾后,连它那不为人知的心事也浸染着绿意。而我置身其中,绿色的冲锋衣像棵倔强的草芽,不管不顾地朝着大地纵深处伸展。
走到三分之一的补给站时,两个大姐因体力不支放弃前行,那位大哥也犹豫不决,稍加休息,我独自上路了。渐渐稠密的雨水终于还是把我带到了泥泞中,许多脚印又被许许多多的脚印所覆盖,不会担心迷路。我与丛林的对话也是从这时真正开始的,彼此不需要任何打探。他对于我是一次鲜活的血液输入地过程,让我亢奋却又平静;而我对于他又是什么呢?我仔细想了一下,也许只是一次别离。来不及熟识便匆匆离去的相见,不是别离又是什么呢,你能说哪一株植物在我经过时没有想挽留我吗?尘世那样远,无论多么强大的事物,此刻都不能将我卷入琐事的漩涡中。在这里,我只需专心致志的走路。泥浆路,沼泽,溪流,横倒在地的朽木,还有马粪,这些可爱的“小障碍”是我一路上最有趣的伙伴儿。陆续有人坐在马背上悠哉悠哉的经过我,还有把人送到终点后空马而归的马夫,极尽所能的告诉我前边的路有多烂,费尽口舌让我以马代步。我才不相信呢,除非他的马亲口跟我说。
可我还是走到了终点:木骡子围场(海拔3700米)。当我翻过最后一个障碍物——两米高的木栅栏,瘫坐在草地上。九月的高原早已没了鲜花,牦牛在吃草,渴了就在近旁的河流饮水。草地四周被雪山环绕,抬头就可以看见高耸入云的四姑娘山,沿着山脚生长着笔直的冷杉林,缠在山腰的薄雾把一切点缀得如同仙境。在我到达后的片刻,重庆大哥也跟了上来,心里嘀咕一句:这样还算你是个爷们儿!
必须在天黑前走到入口,回程的时间很紧。大概走到一半儿的时候,开始头痛,浑身发冷,那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一个被我忽略的问题:高反。加上淋雨,而且在终点时脱掉冲锋衣被山风吹到,又很不幸的发烧了。后半程的路是靠着惯性和意志力走下去的,到最后基本上挪动着向前,体力已经完全透支。不管曾经你的身体和心灵遭受过多么深刻的疼痛,总会被时光磨钝的,当你再回首,只清楚地记得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,却无法具体描述出到底是怎样一种煎熬。
历经8小时29公里的徒步走回客栈时,重庆的两个大姐已经吃过晚饭坐在大厅里,见我脸色很差,忙关切的询问,又帮我盛饭,实在没胃口,谢过之后上楼了。关上房门便大哭起来,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,遭这份罪?想起一些人,却遥远的无法带来任何安慰,觉得委屈,便哭得更加动情。卢老七边敲门边喊:“小卢,你怎么啦?不舒服吗?”我呜咽着说:“没事儿,就是有点头疼”“千万不要洗澡啊,别哭了,睡一觉就好了”。当时已经冷到上下牙齿打颤,头痛欲裂。高反药、退烧药、止疼药,吞下一大把药片,盖了两床被子,后来,又哭了一会就睡着了。
第二天醒来,真的像是梦一场。元气已经完全恢复,继续前往下一站——丹巴。甚至怀疑昨夜的疼痛是否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,但那样孤独地嚎啕大哭却永远坚韧的响彻在我的生命中,从未有过。
那是川藏线上,我的第一次高反,也是唯一一次。